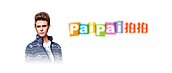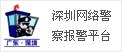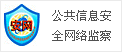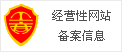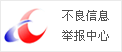□羊城晚報特約記者 馬國川
法國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國沒有再暴力革命過;克倫威爾死后,英國不再革命;南北戰爭之后,美國再也沒有暴力革命……有一次革命就夠了,下面應該考慮如何修正、協調、妥協,這比革命要上算。
許倬云
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30年7月生,求學于臺灣和美國,196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先后執教于臺灣、美國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學,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學貫中西,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等。
為什么改革跑不過革命
羊城晚報:有學者說,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黨人鼓動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實行廢科舉、改官制、設咨議局等改革措施,史稱“晚清新政”。那么,為什么改革跑不過革命呢?
許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著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當時的形勢,不得已而為之。慈禧是一個有手腕有權謀的女人,但是沒有見識,熱衷權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本身固然處在改革和革命之間,看上去似乎有選擇,實際上中國的選擇余地并不多。因為當時維新的力量并不大,維新力量在戊戌政變時遭到了重創,守舊力量重新抬頭,城市里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多少。所以,整體講起來清末改革沒有多少準備工作,無法取得實質進展。例如,雖然各省成立咨議局等民意機構,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羊城晚報:為什么革命力量會在廣東開始壯大起來了?
許倬云:等到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孫中山就往廣東走,一些人也跟著往廣東走,雖然廣東是一個小小地方,沒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國希望之所寄。孫中山在廣東局促一隅,卻終于得到了兩個意外幫助。
第一撥意外的幫助,就是許多沿海地區的留學生,紛紛往廣東聚集。一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幫孫中山做許多事,包括幫助他完成他的理論建構,幫助整理財政,等等。另外一撥意外的力量,就是蘇聯革命以后,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邊的助力,有了組織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裝力量。
羊城晚報:文武兩撥力量終于使得廣東這個革命基地成為氣侯。
許倬云:對,中間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1914年歐戰開始,在華的歐美實業,包括商業工廠都紛紛撤資回國,上海、天津、武漢、廣東等四個地區的民族工商業借機在夾縫里發展起來。再有,在這個時候大批歐美回國的留學生參加了許多歐美人士在中國設立的學堂,將其轉化為中國的教育機構。沿海城市出現不少報紙雜志。中國都市里發展的中層階級、民間資金和知識分子、知識傳播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中國的城市地區,民智漸開,中國得以逐漸走向現代化。
鄧小平的政策
與北伐后南京政府相當類似
羊城晚報:抗戰結束之時,蔣介石聲望如日中天,中國也躋身戰勝國之一,可是不數年國民黨政權就土崩瓦解,這是非常令人費解的歷史結局。
許倬云:國民黨八年抗戰精疲力盡,城市基地幾乎全部喪失。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在政治、經濟和軍事諸項決策中十有九錯。例如,全國希望政府能夠和平建國,能夠實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民主憲政,然而蔣介石以“反共”為號召更加強了集權統治,知識分子推動民主化遭到迫害,學生運動更遭武力壓制,因此人心喪失。最后一根壓死駱駝的稻草是“金圓券”的幣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圓券已成廢紙,全國中產階級為此破產。國民政府的心臟地區民心大失,前線作戰部隊士氣不振。于是,國民黨敗下陣來,共產黨取得大陸的統治權。
羊城晚報:黃仁宇先生曾說過,國民政府重組了中國的上層結構,中共則整合了以農村為主的下層結構。
許倬云:對,在大陸毛澤東繼續走農村路線,以黨的組織力量動員農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夠編組中國廣大的農村,撐起以農民為基礎的國家力量。黃仁宇認為,中共改造了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政府力量從此可以下達農村。這一改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從“大躍進”到“十年動亂”,使得本來可以建設的階段完全浪費。最終輪到鄧小平,才改革開放。鄧小平改革開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當類似。
羊城晚報:鄧的經濟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是相似的嗎?
許倬云:都是經濟市場化,但是也有一個大的差別。毛澤東30年的組織努力,留了一個遺產,就是大陸上有許多小集體出現。城市里有“單位”,鄉鎮也有小集體,它把散亂的農村力量集中成一個過去沒有的集體力量。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后,這些集體力量就變成單位企業、鄉鎮企業的本錢。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鄉鎮企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是僅僅依賴外資。
“南京十年”經驗在臺灣翻版
蔣介石到臺灣時,臺灣已經相當程度城市化,大陸過來的大批城市知識分子繼續舉辦現代學校,學術界也得以繼續發展。臺灣發展濃縮了當年蔣介石沒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經驗在臺灣翻版,而且做得更徹底。當然,在此期間蔣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時期。等到蔣經國執政,接下來也是改革開放。所以,蔣經國和鄧小平兩個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開放途徑。
總起來說,孫中山出現以后中國走了革命的路線,繼續不斷在革命,蔣介石、毛澤東各自繼承了孫中山的一部分。鄧小平和蔣經國個別繼承了毛蔣的一部分,可是鐘擺轉到比較靠中間的地方。這是延續性的“正反合”的過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過程。不管是大陸還是臺灣,前面都有沒走完的過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來的一百年,中國顛顛簸簸,走得確實很辛苦。我個人理解,固然這中間有多次政府的轉換,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戰),整體來看,中國仍然在做連續工作。100年的路是“正反合”的過程,是辯證式的進展,中國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斷革命論”很恐怖
羊城晚報:近兩年大陸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熱議的話題“中國模式”,您怎么看待廣義的“中國模式”?
許倬云: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我們經不起冒險,不能100年或50年繼續走一條路到底。我們把所有的雞蛋擺在一個籃子里,摔一跤雞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雞蛋擺在多個籃子里,最多摔一個籃子。我這完全是從實用的觀點來看“中國模式”。
羊城晚報:對大陸來說,“摔一跤雞蛋全都摔光”的危險確實存在。
許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夠了,下面應該考慮如何修正、協調、妥協,這比革命要上算。
羊城晚報:辛亥革命以后,中國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100年間有近一半時間處于內戰狀態,因此一些人士對辛亥革命提出強烈批評:如果當初不這樣做,而是按著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實行憲政了。據此,他們提出了“告別革命”的觀點。
許倬云:對“告別革命”,我也有同感,因為我的歲數大,看見過內戰的慘烈局面,“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我也聽過十年動亂里,人的尊嚴如何被踐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國經不起再來一次。
我們回頭看,法國大革命慘不忍睹,雅各賓就是大陸十年動亂的微型啊。法國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國沒有再暴力革命過。克倫威爾砍了英國人的頭,克倫威爾曾經以護國主的身份專制獨裁,他死后英國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經驗就夠了,不敢再做了。美國獨立戰爭以后,華盛頓飄然下野。后來又有一次南北戰爭,此后美國再也沒有暴力革命。
老實講,辛亥革命損失不大,軍閥混戰損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損失極大,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浩劫,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損失也極大。以暴易暴,用一個暴力換來另外一個暴力,沒止沒休的,所以我對“不斷革命論”是極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夠了,不要再做了。
馬國川